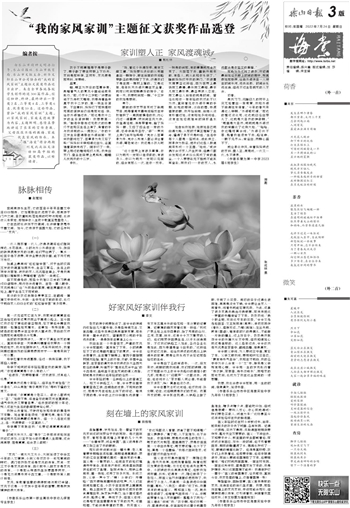■ 赵莺如
世间常存永生花,它的茎自千年来自墨文中自口口相传。它如莲般出淤泥而不染,却常存于门户之间,自孩童呱呱落地起的叮咛与规矩,也许你从未察觉,却相伴你人生数十载直至耄耋老人。
它在古时也许刻于竹简间,也许顺着狼毫书于墨文间。如今,它传颂于祖国大地,它的名字叫——“家风”。
(一)
一代人拥挤着一代人,仿佛浪潮将他们推到岸边,水花四溅。小时与外公外婆住在一处,陈旧的砖房满是岁月的划痕,他们节俭惯了,一瓢水一粒豆子绝不浪费,写作业要去院子里,能不开灯就不开灯。
饭桌上最常说“粒粒皆辛苦”,对于当时仅四五岁的我简直如同天书,生涩又莫名。生活上的艰辛与苦难,被我的家人沉沉担在肩上,于是我常因难以理解而小声嘀咕着“古板”一类词汇。
但不可避免的,那些令我难以忍受的习惯通过口语相传,用行动渗透着我。在老一辈人眼中,家风就是以“俭”为底色的草席,铺在厚重的水泥地上,融于生活又不可或缺。
年幼的女孩逐渐抽条亭亭玉立,在翻阅一篇篇文字中成长,长到一生中无往不前的年纪,也终于明白家人口口念叨的“粒粒皆辛苦”有多可贵。
(二)
第一次见证死亡在九岁,我敬爱的舅舅在他正当灿烂的年纪戛然而止于高速公路上。至今回忆我仍忘不掉他的音容相貌,忘不掉他半蹲在我面前一脸搞怪地变魔术。往事如一张张旧影,如褪色的胶卷悬浮在空中被火星点燃,苍白的灰烬如同那句通知般冰冷无情。
当时的我颓废许久,一度分不清生与死的意义。直到母亲在一天早晨叫嚷着将我带去一个特别的地方,我与她辗转许久,汽车开到城外,我看到围栏里林列的石碑肃穆而安宁——竟是来到了一片公墓。
母亲拉着我走进墓园,经过一块块石碑,我不禁陷入细思。
母亲不知何时将手轻轻搭在我的肩旁,轻声问:“你觉得舅舅是个什么样的人?”
“他很好,”我哽咽着道:“对我很好,对其他人也是。”
舅舅虽然还是个年轻人,但平生尽爱扯些“之乎者也”,口头常挂“君子周而不比”等听不懂的文言文。
母亲说:“你舅舅是个老实人。做什么都讲究个‘正’。”她俯下身,将准备好的鲜花放在墓碑前,语气中忧伤又带着自豪,“他去世时的那个年纪,别人还在为生活的酸甜苦辣烧心呢。”
我转头去看她,才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情绪并不平静。她含着泪继续说:“世事无常,谁也不能保证明天见到晨曦还是意外。但一个人活在这世上,活一天便要做一个正直的人。”
母亲蹲下来抱住我:“也要记得舅舅常道的‘君子’。”
时间太长太久,但“君子”二字却深深地刻在我记忆深处,以至于如今的我遭遇人生困境,还会常常想:若是舅舅,他会怎么做呢?
(三)
“家风”一词太大又太小,大到延续了中华五千年的人文精神,小到父母对孩子一句无意间的唠叨。满门忠烈杨家将是家风的传承,苏洵一家三才子是家风的传承,四代教书人胡家亦是家风的传承,一个是抛头颅洒热血祈愿国泰民安,一个是笔力深厚书写千古文章,一个是教书育人前仆后继。
家风,承载着祖辈的谆谆教诲与殷切希望。家风不仅是一个家族千百年来的智慧,更是民族精神的伟大传承。
(作者系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幼儿保育专业学生)